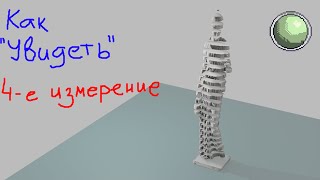親鸞的“大行”思想探析
Автор: 本願海濤音
Загружено: 2025-12-27
Просмотров: 14
关于亲鸾“大行”思想的核心洞见
摘要
本简报深度剖析了德永道雄关于亲鸾“大行”思想的研究,揭示了其复杂而深刻的理论构造。亲鸾的净土教思想始于对传统自力修行(“行”)的根本性否定,但又将“大行”置于其教义的核心,形成了看似矛盾的理论起点。
核心洞见包括:
1. 对传统的继承与颠覆:亲鸾继承了善导与法然的“本愿念佛”思想,但通过提出“如来回向”的概念将其彻底化。他主张,无论是“行”(念佛)还是“信”,其根源均非来自众生,而是阿弥陀如来回向给众生的功德,因此念佛对修行者而言是“非行非善”。
2. 自力与他力的精细分判:亲鸾的独创性在于,他不仅对比了第十八愿(他力念佛)与第十九愿(诸行往生),更对比了第十八愿与第二十愿(自力念佛)。他指出,即使是专修念佛,若抱持“将本愿的嘉号作为自己的善根”的自力执心,也无法获得往生,从而凸显了彻底的“他力信”的决定性作用。
3. 从“易行”到“难信”的转化:亲鸾将法然所强调的“易行”(念佛之容易)转化为“难信”。他认为,正是因为往生之因完全源于“本愿力回向”,才使得众生依靠自力之心难以信受,这种信受的困难反证了如来之力的绝对性。
4. “大行”根据的转移与双重意涵:与将念佛根据置于第十八愿的法然不同,亲鸾将“大行”的根据确立在第十七愿(“诸佛称名之愿”)。这使得“大行”同时具有双重意涵:既指作为其本体的“名号”本身(佛的层面),也指众生的“称名”行为(众生的层面)。
5. “能所不二”的最终综合:针对“大行”究竟是指名号(所行)还是称名(能行)的争论,最终的理论综合是“能所不二、镕融无碍”。其根本依据在于,无论是名号还是称名,都是如来为救度众生而不断从佛侧向众生侧发起的“一体化运动”的表现。这一运动本身即是“大行”,而众生无疑之信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在众生身上显现的关键契机。
一、 亲鸾“大行”思想的内在矛盾与核心议题
亲鸾的净土教思想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悖论之上:一方面,它彻底否定了传统佛教中依靠个人修行之功德(“行”或“修行”)达成证悟的路径,视一切人为的善行为“杂毒之善”;另一方面,它依然将“行”作为其教义体系的核心,其主著即为《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》。
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揭示了亲鸾思想的核心议题:
否定之上的肯定:亲鸾首先否定了“自证教”(依靠自我修行证悟),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“救济教”(依靠佛力救度)。对他而言,放弃圣道门的“教行证”之后,必须重新确立净土门的“教行证”。
“大行”的双重性:“大行”这一概念因此具有双重面向。它既与传统的“行”在意义上完全不同,因为它否定了人的“造作”;但同时,它又被认为是“行”所具有的本来意义的最高体现,因为它能引导众生获得证果(往生净土)。
中心课题:因此,理解亲鸾思想的关键在于回答两个问题:他所说的“大行”,在何种意义上已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“行”?又在何种意义上依然能够成立为“行”?
二、 从善导到法然:“本愿念佛”的演变
亲鸾的思想继承并深化了由善导至法然的“本愿念佛”传统。
善导的奠基:
念佛的独立价值:善导虽然承认《观无量寿经》中的定善、散善二行是往生的“要门”,但他强调,若依阿弥陀佛的本愿(第十八愿),“称名念佛”才是众生应修的“正定业”。他将原本在圣道门中仅为方便之行的称名念佛,提升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往生之行。
无条件的行:善导将第十八愿的“乃至十念”解释为“下至十声”,强调了念佛次数的不确定性。他亦强调“行住坐卧,不论时节久近”,指出了念佛行仪的无限定性。这种打破常规律法条件的“行”,其成立的唯一根据是“顺彼佛愿故”,即它的价值不在于称名的功德,而在于本愿本身。
法然的彻底化:
专修念佛:法然对善导的思想进行了“废立”,废除了定散二行,只选择称名念佛作为往生净土的唯一绝对业因,从而创立了独立的净土宗。
功德归于名号:法然深刻洞察了善导思想的真意,提出了“不回向的念佛”和“他力的念佛”。他在《选择集》中明确指出,念佛之所以能带来往生的果报,其功德根源在于“名号”本身。“名号是万德所归”,一切功德“皆悉摄在阿弥陀佛名号中”。
善导与法然都将念佛往生的根据求于本愿,这表明他们所倡导的“称名正定业”,已经与依靠自身修行功德获得果报的传统“行”的观念产生了本质区别。
三、 亲鸾的革新:如来回向的行与信
亲鸾在继承法然教诲的基础上,通过“如来回向”的理论,将他力思想推向了极致。
行信皆由如来回向:
亲鸾主张,不仅是往生之因的“行”(念佛),与之不相离的“信”也同样是如来回向给众生的。其著作《教行信证》开篇即言:“谨按往相回向,有大行,有大信。”
正因为“行”是如来回向的,所以才能称之为“大行”,并彻底消解了众生一方“造作”的意义。亲鸾认为,所谓的行,并非众生“造作”或被动地“被造作”,而是“如来的造作成为众生的进趣(往生)”。
基于此,亲鸾得出了著名论断:“念佛对修行者而言,既非行也非善”,将念佛的非功利性、非造作性推到了顶点。
第二十愿的别开:精细分判自力与他力:
亲鸾的独创性体现在他对第十八、十九、二十愿的对比上,尤其是通过辨析第十八愿与第二十愿,阐明了他力念佛与自力念佛的根本区别。
他将第二十愿的“植诸德本”解释为一种自力的念佛。这种念佛的修行者极为纯粹,一心念佛,但其内心深处仍存在着**“将本愿的嘉号作为自己的善根”**的自力执心。
正是因为这种“助正间杂,定散心杂”的自力之心,使得名号(本愿)的真实性无法完全发挥。这表明,本愿之力能否显现,取决于行者的“信”是否是纯粹的他力信。
从“易行”到“难信”:
善导和法然将第十八愿视为“念佛往生之愿”,而亲鸾则将其视为“信心中心之愿”。他认为,善导、法然对念佛的归依本身就包含了对本愿的全体性的信赖。
亲鸾将法然所说的“易行”念佛,理解为一种“难信”的法门。其逻辑在于:往生的正因完全是“本愿力回向”,而众生由于根深蒂固的自力执心(第二十愿之心),极难真正信受这一事实。
因此,“易行”之所以为“易”,与“难信”之所以为“难”,其根源都在于“本愿力回向”这一事实本身。信受如来加持力的困难,反向彰显了自力心的顽固与他力救度的绝对性。
四、 “大行”的根据:第十七愿与名号、称名之关系
亲鸾将“大行”的理论根据从法然所依据的第十八愿,转移到了第十七愿(“诸佛称名之愿”),这带来了深刻的理论变化。
“大行”的定义与问题:
《教行信证》行卷将“大行”定义为“称无碍光如来之名”。但其后的论述大量引用关于“名号”本身的经论释文,似乎又将“大行”归于“名号”自身。
这引发了核心问题:亲鸾所说的“大行”,究竟是指众生的“称名”行为,还是指作为佛法体的“名号”本身?
第十七愿的双重解读:
亲鸾对第十七愿给予了多重名称,可以分为两类:
1. 从诸佛的层面:“诸佛称名之愿”、“诸佛称扬之愿”,意指此愿所誓的内容是诸佛所称赞的“名号”。
2. 从众生的层面:“往相回向之愿”、“选择称名之愿”,意指此愿所誓的内容是众生往生净土的正业——“称名”。
这表明亲鸾在第十七愿中同时看到了“诸佛的称名”与“众生的称名”两重含义,并进一步引申出“名号”与“称名”的关系问题。
名号与称名的不二关系:
一种普遍的解释是,众生的“称名”是在“闻”的层面来理解的。即众生口中称念佛号的行为,实际上是在聆听诸佛所称扬的阿弥陀佛之名号。这与亲鸾将名号解释为“本愿招唤的敕命”相符。
最终,问题归结为名号与称名的关系。作者德永道雄认为,亲鸾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,而是将两者视为一个不二的整体。无论是名号还是称名,其根源都在于如来的大悲摄化之心(本愿)。
因此,“大行”的双重性得以统一:
名号即大行:强调名号本身是“大行”,突显了其绝对的真实性(“净土真实之行”)。
称名即大行:强调众生的称名是“大行”,体现了这一真实性在众生身上的具体显现,也是对法然“专修念佛”的继承(“选择本愿之行”)。
五、 最终综合:能所不二与如来的单向运动
围绕“大行”是指称名(能行)还是名号(所行)的问题,真宗学者间形成了“能行派”与“所行派”的长期论争。
能行派与所行派的局限与融合:
能行派:强调众生的“称名”,旨在从人的主体经验层面把握“大行”,但有将念佛律法化的风险。
所行派:强调“名号”本身,旨在确保“大行”完全属于如来,但有将名号抽象化、脱离现实经验的风险。
两派最终不得不走向融合。能行派承认称名是法体名号的“回入”,所行派也承认名号必须在众生的称名中“显现”。这一融合最终被概括为 “能所不二、镕融无碍”。
“不二”的根源:如来的一体化运动:
作者指出,以往的论争未能充分究明“能所不二”的一体性根源何在。
亲鸾思想中的“一体性”(如机法一体、佛凡一体)绝非众生本自具足,而完全是从佛的侧面发起的运动。众生与佛的断绝是前提,而一体性是佛为打破这种断绝而采取的行动。
这一行动在因果世界的表现即是:作为“真如”的法性法身,化现为方便法身(阿弥陀佛),再进一步通过法藏菩萨的发愿、修行、成佛这一过程,才得以直接与众生发生关联。
因此,本愿及其成就(名号),是已从果向因的如来,为了与众生一体化而发起的**“更进一步的、持续不断的运动”**。
结论:
这个**“从如来到众生的一体化作用”本身,就是“大行”**。
因此,作为这一作用本身结晶的“名号”是“大行”,而这一作用在众生身上具体显现的“称名念佛”同样也是“大行”。二者不可分割。
能使这一作用在众生身上成立的关键时刻(Moment),即是亲鸾所说的“无疑盖无杂”的纯粹他力之信。

Доступные форматы для скачивания:
Скачать видео mp4
-
Информация по загрузке: